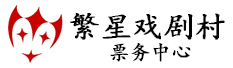话剧《山上的耶伯》:古老喜剧在京腔京韵中焕发新生
更新时间:2025-12-07 07:40 浏览量:25
“黄粱炊烟尚未散,蟒袍底下破袄藏。烟袋敲醒荒唐梦,西山萝卜依旧香。”当1903年北京西郊的晨雾漫过舞台,旗人叶伯醉卧街头的身影,与丹麦剧作家霍尔堡创作于300年前的经典喜剧形象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当代观众在笑声中获得思考和启悟。由邵泽辉改编、导演的话剧《山上的耶伯》,作为献礼中丹建交75周年之作,以其流畅的跨文化转译,让古老喜剧在京腔京韵中焕发新生,成为当代小剧场话剧跨文化改编与本土化表达的典范。
影响了安徒生、易卜生等创作的丹麦与挪威文学之父、被誉为“北欧莫里哀”的喜剧大师路德维希·霍尔堡,其经典喜剧《山上的耶伯》是北欧启蒙文学的经典之作,该剧通过讲述农民耶伯因偶然机会获得财富和权力后人性异化的故事,讽刺了社会的等级制度、伪善和人性弱点。邵泽辉导演没有简单复现这一古典文本,而是捕捉其中的永恒内核和普世话题,进行大胆而巧妙的本土化改编,并赋予其一个极具中国意蕴的副标题——“西山醉梦录”,用一场啼笑皆非的身份置换,在闹剧外壳下表达关于存在本质的深沉叩问。
该剧故事背景从丹麦乡村移至清末北京城西山脚下,主角耶伯变为佃户叶伯,贵族“男爵”化为爱找乐子的“毓贝勒”。贝勒爷因无聊将醉酒昏睡的叶伯抬回府中,给他穿上华贵服饰,谎称其是真贝勒,让叶伯在精心编织的黄粱梦里体验了三天富贵人生。叶伯在权力幻觉中不愿意醒来,为了延续美梦甚至想“杀死真正的自己”。剧中引发的关于“自我、本我、超我”的探讨,构建出一面映照社会的哈哈镜,将人们对身份标签的迷信与盲从,展现得淋漓尽致。
整个演出笑点密集,风格轻快幽默,用喜剧糖衣包裹严肃的哲学追问,在嬉笑怒骂间尽显荒诞本质。京味方言的融入、烟袋锅与锦绣华服的视觉碰撞、贝勒府与平民院的场景切换,让丹麦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通过京腔京韵的市井烟火落地生根,既保留了霍尔堡喜剧的核心魅力,又让中国观众在欣赏和理解时毫无距离感,实现了“外来经典”与“本土文化”的无缝衔接。
舞美设计吴蕾与灯光设计曲明共同构建的视觉体系,成为推动叙事的重要表意符号。舞台上,西山的剪影始终笼罩在朦胧光影中,既像是叶伯醉梦中的精神原乡,又象征着身份的模糊边界——当贝勒府的锦绣屏风与平民家的土炕同台并置,虚实空间的交错恰如其分地呼应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核心命题。
演员们以松弛而精准地表演,完成了喜剧张力与人性深度的平衡。陈磊扮演的叶伯从醉后的懵懂接受、掌权时的虚荣膨胀到清醒后的迷茫失措,三个阶段的转变层次分明,既有着市井小人物的滑稽可爱,又暗藏着个体在身份错位中的被动与无助。
“到底是黄粱一梦,还是人生如戏?”这个贯穿全剧的追问,从清末旗人叶伯的困惑,延伸到每个现代观众的生存反思。叶伯的身份置换,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自我”与“角色”的哲学实验——当社会赋予的标签被强行更换,个体的本质是否会随之改变?而毓贝勒与叶伯的身份互换,更是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自我”,不过是社会角色赋予的惯性表演。这场西山脚下的醉梦,恰似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个在社会角色中挣扎的灵魂:我们究竟是在扮演某个角色,还是被角色吞噬?
记者: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