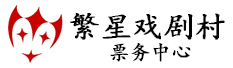余秋雨最新演讲: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文化正在遭受巨大的委屈
更新时间:2025-12-30 09:37 浏览量:58
天门山文学
余秋雨2025上海戏剧学院 80周年校庆发言稿(修正版)
大家好!学校安排我在这个大会上发言,却没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那我必须自己找一个,不然讲起来总觉得不顺。而这个理由很快就找到了 ——
今天是母校建校 80 周年的日子
。
曾经有过很多位院长,在如今健在的院长当中,我的辈分最高。我辞职之后,后面又有四任院长接任。按照我们的语言习惯,总喜欢把前任院长称作 “老院长”。这么算下来,我是四任之前的院长,这 “老” 字就得叠加几层,我就成了 “老老老老院长”。
有了这个身份,我觉得自己讲话也算有了一点点底气。站在这个舞台上,当我宣布自己是 “老老老老院长” 的时候,心里生出了一种
时间的幽默感
。为什么呢?这个剧场,正是在我任职期间启用的。我当时在这里讲话时,身上顶着很多 “最年轻” 的头衔,和现在的 “老老老老” 正好相反。
当时公开报道都说,我是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又是全国最年轻的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当然,“最年轻” 的头衔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是,我当时的形象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小,所以闹出了不少好玩的事。
比如,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在行政级别上是正厅级官员,按规定要去隔壁的华东医院参加干部健康检查。那时候的厅局级干部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我夹在他们中间,看起来特别像个秘书。终于轮到我时,华东医院的一位护士高声喊道:“检查身体,首长自己来!” 她是对着我说的,我只好非常抱歉地低声跟她说:“我就是首长。”
我为什么会觉得抱歉?是为自己的年龄抱歉,当时实在显得太年轻了。
大家肯定会问:既然那么年轻,为什么不把院长这个职位好好做下去呢?
我当初提出辞职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领导都不同意。我讲了很多理由,他们听起来却一头雾水。就这样,我前后辞了整整 23 次,领导们最后实在拗不过我,才点头同意。他们把比我大 12 岁的胡妙森院长提拔为我的接班人,我就这样离开了。
大家肯定觉得奇怪:为什么非要执着地辞二十几次职?今天我可以把理由说清楚了。当时,一件天大的事摆在了我的眼前,在我看来,这件事比做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重要得多。
是什么事呢?当时我强烈地感受到,
中华文化正在遭受巨大的委屈
。可凡是有点名气的文化人,写文章时都在批判 “丑陋的中国人”,都在谈论 “文化的劣根性”。
中华文化当然有不少缺点,但在做院长之前,我已经写了很多书。通过我的研究,我认定中华文化有着极其伟大的地位。可我没法和那些人辩论,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足够的实证支撑我的观点。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
亲自去寻找一千年前中华文化的伟大遗址
,把它们一点点描写出来,再一步步分析透彻。
然后,用这些遗址作为点,连成线、铺成面,绘制出中国第一部文化地图。但光有这份地图还不够—— 一种文明的伟大,必须和其他文明对比才能凸显。所以,我还得去人类其他古文明的遗址,做一次对比性的实地考察。
这么一来,我要走的路就太多了。但在我看来,这件事刻不容缓。因为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如果总觉得自己的民族是丑陋的、自己的文化是有劣根性的,不仅会挫伤我们自己的心灵,更会对整个社会舆论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所以,我必须去做这件大事。
但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能真正读懂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古代遗存,又能亲手找到那些遗址的人,往往是老学者;可老学者的身体,大多经不起长途跋涉。而身体能扛得住的年轻人,又缺少明确的考察目标、清晰的考察图谱,更没有足够的考察动力。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们未必都具备
无畏的勇气
。这种“无畏”,甚至包含了直面生命威胁的决心。比如我们要去的那些古文明遗址,大多处在恐怖主义盘踞的区域,要把这些地方走遍,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站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办公室的窗前,认真地想:从学识、年龄、勇气这三个条件综合来看,当时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符合要求。
所以,我必须出发,义无反顾地出发。
那么,这趟远行最后带来了什么成果?我不是在这里自鸣得意,只是想借着这个场合,向母校汇报我当年出走的理由 —— 这份理由,只能用这些成果来证明。今天正好有很多领导在场,我就多讲几句。
至少有这么几方面的成果:考察期间,我写下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这些书。这些书不仅打动了我的读者,更首先打动了全世界的华人。因为我在讲述中华文明古代辉煌的同时,也守护住了他们的尊严。所以这些书很快登上了全球华文书排行榜的榜首,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全球各地华人读书会的首选书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这一趟又一趟的远行,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我被评为 “全球走得最远的人文学者”“当代最勇敢的文化探险家”。于是,很多国家向我发出演讲邀请,请我去当地的大学、重要机构分享见闻。就这样,我的旅行又有了新的方向 —— 为演讲而远行。
第三点,在这两次考察的基础上,我梳理出了自己的中国文化史观。这套文化史后来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的博士课程。课程在喜马拉雅平台播出后,收听率很快就超过了 1 亿。刚才有几位校友告诉我,他们这两天还在听这个课程。
这几件事加在一起,我想我可以向母校交差了:当年的辞职,是值得的;也可以向当年的领导们说明:当年辞职的理由,是充分的。
我走得很远,也走了很久。但无论是在中东大沙漠的战壕边,还是在南亚恐怖主义猖獗地区的生死悬崖旁,每当遇到最艰难的时刻,我总会想起一个地方 —— 我的出发地,
上海华山路 630 号
。
那段日子的困难和艰险,实在难以言说。当时有位大画家陈逸飞,得知我要去中东那么危险的地方,而且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独自前往,特意为我赶制了一件衣服 —— 就是我今天穿的这件。他说:“你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一定要穿上我给你做的衣服。”
陈逸飞先生去世已经 20 年了,今天我特意穿上这件他做的衣服,告诉我的母校:我走完了这趟旅程,全程走完了。
我离开之后,上海戏剧学院会变成什么样呢?我走得太远,其实不太清楚;要写的东西太多,也没有精力去打听。但我心里知道,母校一定会越来越好。
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在我辞职远行的一年后,于和伟踏进了校门;两年后,李冰冰来了;三年后,马伊琍入学;四年后,王景春走进了校园;六年后,冯绍峰成为了这里的学生;九年后,宋佳来到了上戏;十年后,胡歌踏入了校门;十一年后,雷佳音入学;十三年后,江疏影成了这里的一员;十四年之后,王传君也来了。
这个名单太长了,如果再跳到新一代,我辞职 21 年后,彭昱畅也踏进了母校的校门。
你们肯定觉得奇怪:你这样一个常年在外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离开后入学的新生名字记得这么清楚,甚至连他们入学的时间都能说出来?我的回答是:
出于尊敬
。
大家可能会想,在校庆这样的日子里,尊敬应该是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你作为老师,为什么要对年轻的学生表示尊敬?
这正体现了我的一个理念:
教与学之间,是一场生命与生命的互动与交流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最优秀的演员,靠技巧训练是培养不出来的。他们往往拥有一种 “有机天性”—— 我们简单点说,就是 “天性”。这种天性,往往被社会生活的层层外壳包裹住了。
我们无论是老师还是导演,要做的事,就是把他们身上的重重障碍一层层剥除,让他们美丽、美好的天性慢慢展现出来。这个剥除障碍的过程,就是老师要做的事,就是导演要做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变得越来越精彩,老师也会受到感染、受到冲击,实现自我提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老师是另类的学生,学生是另类的老师
。
师生之间是这样,学校与学生之间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校友、毕业生、在校生,你们都用自己美好的艺术天性,沉淀成了上海戏剧学院这座高贵的门庭。所以,我必须向你们表示尊敬。
三年前,我曾经把这个名单说给一批特殊的来访者听。他们听完之后,也露出了尊敬的神情。
这批来访者,是上级机关派来的督导组成员。他们来检查上海戏剧学院各方面的工作,也会听取各种举报意见。他们在巡视学校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书本里认识的那个我,竟然和这所学院有着很深的渊源。于是他们提出,希望在巡视结束后能见我一面。
那次见面的场景,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聊得非常愉快。我先问他们:“你们最早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记得,一个是学医的,一个是学金融的。
我说:“你们的母校都非常大,和你们的学校比起来,上海戏剧学院实在太小了。你们在检查工作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现:这所学校的课程不够严谨,教材也不够完整。你们在听取意见的时候,也一定听到了不少声音 —— 我们学院的好多学生,甚至老师,喜欢骂骂咧咧、喜欢胡说八道,而且还是用莎士比亚的腔调来胡说八道,你们听着肯定觉得闹心。”
“但是,请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庭院。这些年,这里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人。”
接着我就念了那个名单。他们听完都很惊讶,连连说:“这个是你们的学生?那个也是你们的?” 我说:“这还不够呢,我讲的只是表演系的学生。我们学院还有很多其他专业,而且我刚才说的,都只是我离开学校之后入学的人,在这之前,还有更多响亮的名字。”
我又说:“你是学医的,研究的是如何医治病人的身体;而这个庭院里的人,研究的是如何滋养人们的心灵。你是学金融的,研究的是货币的流通;而这个庭院里的人,研究的是人类情感的流通。”
我知道,那次见面让他们非常兴奋。我相信,他们向上级机关汇报巡视成果的时候,一定会对上海戏剧学院给出更多正面的评价。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如果他们今年再来,我会给出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我会问他们:“你们看过于和伟主演的《沉默的荣耀》吗?他用自己的表演艺术,震动了全中国 ——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都被这部作品打动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太深了:几十年的邻居互不相识,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很少往来。但这部作品里,七十年前的几秒钟沉默,能让今天的年轻观众肃然起敬;海峡对面的一个眼神,能让海峡这边最粗心的观众也泪如雨下。
这让大家突然明白:天地之间,还有一种能够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我很早以前在《世界戏剧学》这本书里说过:戏剧的最高魅力,就是让千千万万素昧平生的观众,感动得像同一个人;让万般冷漠的现代社会,获得共同的精神热能。这样一来,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悄悄提高几分。
我说,这就是戏剧艺术的力量,这就是表演艺术的力量。
既然提到了《沉默的荣耀》,我就必须再多说几句 —— 因为这部作品和我们的校庆息息相关。
这部作品的第一男主角于和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第一女主角吴越,也是上戏的校友;剧中那个戏份很重的叛徒云泰,同样拥有上海戏剧学院的学历。最有意思的是,这部剧的总制片人马宗俊,他是自学成才的上海工人,但他在填写最高学历时,写的是: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自由进修生
。
他所谓的 “自由进修生”,就是随便在这个院子里听听课,结交几位自己信任的老师 —— 比如我。学校没有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学生名册里,但他却把上海戏剧学院,当作了自己最重要的文化背景。
一部这么成功、在全国引起轰动的作品,方方面面都和上戏有关。那上海戏剧学院是什么态度呢?
我的回答是:
他们的表情非常冷静
。没有宣传,没有夸张,没有炒作,也没有庆祝。戏剧学院的老师面对学生的荣耀,只是在沉默中微笑;整个母校面对学生的优异成绩,也只是在微笑中沉默。
所以我想说,很想用这部作品的名字,来形容上海戏剧学院的校风 —— 那就是
沉默的荣耀
。
我想,这种校风,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校风,更是天下所有大气的教育机构共有的校风:面对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我们能做的,只是沉默着微笑。
母校的这种校风,能不能给我们的学生和毕业生带来一些启发呢?我刚才在休息室里,见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校友,作为老师,我也想叮嘱大家几句。
我刚才说了你们很多好话,现在也请允许我用冷静的语言,给你们提个醒。
我想说:你们的年龄、你们的才华,让你们现在正处在风光无限的阶段。但你们要清楚,你们所拥有的风光,和你们专业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如果拿你们内心的品德高度、拿你们的文化素养,去和其他行业最优秀的人才相比,你们应该明白:你们所享有的风光,强度很可能是被夸张了的。
而这种夸张,往往会带来另一种夸张 —— 当风光变成风浪的时候,你们所遭受的冲击,也会被无限放大。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作为老师,我的建议有两点:第一,
对于任何风浪,都不要太当一回事
;第二,
对于任何风光,也不要太当一回事
。
对于风浪不以为意,我相信聪明的你们都能做到;但对于风光不以为意,你们可能还差一点距离。
你们要明白:你们的风光,是社会给予你们的褒奖,是你们应得的。但恰恰是这份褒奖,加重了你们的精神负担,让你们失去了很多轻松。
所以,你们在享受风光的时候,内心要看淡它、看清它,甚至要放下它。过些年,最好还能忘记这些风光。这样一来,你们的人生才会真正轻松。
能做到吗?我想,我们在座的老一辈艺术家,其实都深有体会,他们在很多方面,早就做到了这一点。
我至少能举一个例子:在你们学习表演之前,有一位艺术家已经拿遍了中国所有舞台剧和电视剧的最高奖项,甚至还获得了国际终身成就奖。但他在拿到每个奖项的第二天,就把荣誉放下了;过不了几天,就忘得一干二净。
正因为他自己忘了,他的老朋友也跟着忘了;他的新朋友,更是完全不知道这些事。完全不知道,好不好呢?我觉得很好 —— 他过得轻松又优雅,没什么不好。
你们的年纪也慢慢大了,眼前会浮现出两种人生形象:一种是挂满荣耀的成功人士,一种是衣衫朴素的缥缈背影。两种形象都不错,但毫无疑问,
后一种更有诗意
。
海德格尔说过:成功的人士,也应该尽量过有诗意的生活。这句话,供你们参考。
我们在座有很多我的老朋友,你们肯定会想:在 80 周年校庆这样的重要场合,你作为 “老老老老院长”,怎么把重点都放在了你离开之后才入学的年轻人身上?这样对历史,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
当然,听起来好像是有点不公平。但我的理念是:
对历史最好的回答,就是当下
。
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一所学校,都是如此。说大一点:如果过去的历史能够决定现在,那么比中华文明更古老的埃及和伊拉克,应该在当今世界拥有更强的话语权。但谁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正是靠着当下的强大,才为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打上了一束追光。
所以,上海戏剧学院的辉煌历史,当然不能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年轻名字来概括。但毫无疑问,
他们青春的肩膀,足以扛起这八十年的重量
。我想,即便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创始者顾毓琇先生,也会同意我这番话。
我刚才说,对历史最好的回答是当下。但紧接着还有一句话:
对历史最困难的回答,是未来
。
一提到未来,我们都会有点慌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 AI 技术、人工智能,几乎已经可以替代戏剧艺术的方方面面了。
今天是校庆,如果大屏幕上放出爱因斯坦演唱上海戏剧学院校歌的画面 —— 而且用上海话唱、用河南话唱都毫无违和感,口型精准、表情自然 —— 这在技术上已经完全可以实现了。
不只是舞台美术和表演艺术,就连导演、编剧,都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所以很多记者说:人工智能迟早会替代人类,希望到那个时候,它们能对人类好一点。
这话听起来有点让人沮丧,但我也发现了让人乐观的一面。这些年,我和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院士有过深入的交流。我问他们:“现在人工智能能替代人类的很多能力、很多职业、很多工作。请问,你们觉得哪一种能力、哪一种职业,最难被替代、最晚被替代?”
这些科学家思考了很久,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
最难被替代的,是艺术家的原创灵感
。
他们的回答,让我非常兴奋 —— 因为艺术家的原创灵感,和我们的戏剧艺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在谈论戏剧的未来时,不必感到沮丧。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人类的最后尊严。
当然,这个问题也引发了我很多学术思考。比如很多人说:戏剧的未来,一定和戏剧的起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就像宇宙大爆炸时期产生的暗物质和物质,决定了宇宙的今天和明天一样 —— 这是一种元宇宙的结构。
这个话题讲起来很复杂,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展开细说了。我心里有一个时间节点:
再过20 年,到上海戏剧学院百年校庆的时候
。
如果到那个时候,这所学院还存在,那就证明: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对峙中,人类并没有完全溃败。
那个时候,于和伟老了,我们在座的各位也都老了,就连田沁鑫院长也上了年纪。而那时,在舞台上创新戏剧的人,很可能是这几天刚刚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我们对他们的创造物,可能看不明白,或者半懂不懂。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我前面说过:对历史最好的回答,就是当下。
我们的当下,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社会转型。在这次转型中,经济和科技扮演了主角,它们的贡献非常巨大,但也有小小的遗憾 —— 它们都比较枯燥,缺少审美价值。
而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幸在这个重要的时代,从事艺术创造、享受艺术创造。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这就像在唐代写诗、在文艺复兴时期作画 —— 尽管我们的水平比不上李白、杜甫,比不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但
伟大与我们有关,美与我们有关,亿万民众的喜怒哀乐与我们有关,人类的终极尊严与我们有关,上海戏剧学院与我们有关
。
我们,还求什么呢?
正因为这样,在我们今天,或是接下来两天的校庆活动中,我们应该快乐,应该高兴,应该愉悦。
好了,我讲完了。谢谢大家!